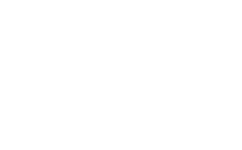


女性主義第一、二波浪潮期間,西方國(guó)家所舉行的女性主義維權(quán)運(yùn)動(dòng)。
當(dāng)“Feminism”這個(gè)英文單詞在上世紀(jì)八十年代流入中國(guó)時(shí),出現(xiàn)了兩種譯法,“女權(quán)主義”和“女性主義”。李銀河后來(lái)說(shuō),“Feminism”在中國(guó)翻譯出了兩個(gè)詞,本身就暴露出了問(wèn)題。
即便是“Feminism”在國(guó)內(nèi)出現(xiàn)已經(jīng)20多年后,人們?cè)谔崞疬@個(gè)詞時(shí),也還是將“女權(quán)主義”和“女性主義”混淆在一起進(jìn)行使用。五年前在一次采訪中,北京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國(guó)際關(guān)系學(xué)院李英桃教授說(shuō)道:“中國(guó)人一談起性別問(wèn)題,常常會(huì)聲明‘我不是女權(quán)主義者’,好像自稱(chēng)女權(quán)主義者是丑陋的事。在很多中國(guó)人眼里,女權(quán)主義常常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此時(shí)距離戴錦華大聲宣布自己是女權(quán)主義者已經(jīng)過(guò)去了十余年。
上世紀(jì)的女權(quán)主義
從“鐵娘子”到“女人味”
“女權(quán)主義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有一個(gè)很有意思的特點(diǎn),即最初由李大釗、陳獨(dú)秀等男性推動(dòng)和倡導(dǎo)。近百年來(lái),經(jīng)歷了數(shù)次革命,中國(guó)女權(quán)的發(fā)展比許多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都快。如今,一種新女性主義在中國(guó)悄然登場(chǎng)。”在五年前的同一個(gè)采訪中,李銀河對(duì)中國(guó)的女權(quán)主義如此概括。
王政和沈睿可以算是真正的中國(guó)第一代女權(quán)主義者的代表,這些人大都經(jīng)歷了改革開(kāi)放前的“鐵娘子”時(shí)代和改革開(kāi)放初期“女人味”的時(shí)代,她們也都經(jīng)歷過(guò)女性意識(shí)的焦慮。
在改革開(kāi)放以前,“男女平等”一直是被國(guó)家壟斷的議題,那時(shí)婦女地位的上升在日后被稱(chēng)作“國(guó)家恩賜的婦女解放”。它的特點(diǎn)是自上而下從階級(jí)出發(fā),忽視男女性別差異,使當(dāng)時(shí)“鐵娘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八十年代,改革開(kāi)放后資本在中國(guó)重新分化,資本市場(chǎng)化伴隨的是資源大量流向男性的父權(quán)回潮。再加上革命和階級(jí)的話語(yǔ)被否定,也讓改革開(kāi)放后的一代對(duì)“男女平等”產(chǎn)生了“寒蟬效應(yīng)”。女性急著尋找自我,從“鐵娘子”的形象中解脫出來(lái),尋找回歸自然的“女人味”。
九十年代,世界婦女大會(huì)的到來(lái)成了女權(quán)主義的新起點(diǎn)。“社會(huì)性別(gender)”的概念被帶入中國(guó),也第一次把婦女權(quán)利納入了人權(quán)的范疇。“社會(huì)性別”的概念挑戰(zhàn)了八十年代男女性別自然化的“本質(zhì)主義”思維,而把性別歸為社會(huì)構(gòu)建的結(jié)果,這也形成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女權(quán)主義的根本動(dòng)力——消滅操演著性別不平等的社會(huì)運(yùn)作機(jī)制。王政和沈睿,分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到國(guó)外接受了女權(quán)主義相關(guān)的教育,開(kāi)啟了各自的女權(quán)主義啟蒙道路。
本世紀(jì)的女權(quán)主義
不再滿足于自我賦權(quán)
隨著中山大學(xué)的教授艾曉明在2003年創(chuàng)立中山大學(xué)性別教育論壇,并帶領(lǐng)學(xué)生排演女權(quán)主義話劇《陰道獨(dú)白》,中國(guó)的女權(quán)主義思潮逐漸地走向了大眾。柯倩婷、李思磐均受到了艾曉明的影響,在不同領(lǐng)域舉起了“女權(quán)主義步入主流話語(yǔ)”的大旗。2009年,婦女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女權(quán)之聲”作為NGO創(chuàng)立,負(fù)責(zé)人便是現(xiàn)在青年女權(quán)行動(dòng)界的精神領(lǐng)袖“呂頻”。多元化、訴求普通人參與是第二代女權(quán)主義的特征,她們與媒體互動(dòng)頻繁,策劃文化活動(dòng),高調(diào)發(fā)表女權(quán)主義言論,力圖影響年輕人的觀念。
2012年,青年女權(quán)倡導(dǎo)小組BCome在北京成立。以肖美麗、趙思樂(lè)和艾可為代表的新一代女權(quán)主義者,被媒體稱(chēng)作“青年女權(quán)行動(dòng)派”。她們多為85后,成長(zhǎng)在世婦會(huì)一代所倡導(dǎo)的與公共空間緊密結(jié)合的女權(quán)土壤中。“青年女權(quán)行動(dòng)派”充滿了創(chuàng)造性和行動(dòng)力,有時(shí)甚至有些荒誕。她們把平權(quán)倡導(dǎo)訴諸話劇和行為藝術(shù)當(dāng)中。其中最引人側(cè)目的平權(quán)行動(dòng)有倡導(dǎo)反家暴的“帶血的婚紗”街頭行為藝術(shù)、抗議高考招生性別歧視的“剃光頭亮瞎教育部”行動(dòng)、呼吁男女廁所廁位比例不均的“占領(lǐng)男廁所”等行動(dòng)。這些行動(dòng)給她們帶來(lái)了不少年輕的支持者,也有的放矢地推動(dòng)了國(guó)家政策上的一些改變。她們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自我賦權(quán),她們更多地想要影響制度,做游戲規(guī)則制定的參與者。
從國(guó)家恩賜的婦女解放,到人權(quán)范疇內(nèi)的婦女權(quán)力倡導(dǎo),女權(quán)思潮在中國(guó)一代又一代薪火相傳著。她們不斷地發(fā)出聲音,一點(diǎn)一滴地挑戰(zhàn)著男權(quán)結(jié)構(gòu)的陳規(guī),影響著人們的觀念。她們的聲音聽(tīng)來(lái)并不溫柔甜美,偶爾尖銳,甚至振聾發(fā)聵。
“在我們這里,音量刺耳是應(yīng)對(duì)裝聾作啞的”,女權(quán)主義作家張念說(shuō)。
【鏈接】
女權(quán)主義在世界
人類(lèi)社會(huì)史上,人權(quán)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歷史,但人權(quán)概念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內(nèi)并不包括女權(quán)。1791年法國(guó)大革命的婦女領(lǐng)袖奧蘭普·德古熱發(fā)表《女權(quán)與女公民權(quán)宣言》,女性主義運(yùn)動(dòng)拉開(kāi)序幕。“宣言”開(kāi)宗明義,認(rèn)為“婦女生來(lái)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權(quán)利。”兩年后這個(gè)宣言的作者就被她過(guò)去的男性同黨推上了斷頭臺(tái)。
女性主義批評(píng),作為一種文本批評(píng)或話語(yǔ)批評(píng)的時(shí)尚,則遲至1960年末的政治動(dòng)蕩時(shí)期才在西方出現(xiàn)。其實(shí)早在上個(gè)世紀(jì)初,當(dāng)代女性主義批評(píng)的啟蒙者之一,弗吉尼亞·伍爾芙就已經(jīng)注意到,在主流話語(yǔ)中缺乏婦女的聲音,大部分文學(xué)作品中的女性其實(shí)都只是說(shuō)著男性作家要她們說(shuō)的話,做著男性作家要她們做的事。
婦女解放運(yùn)動(dòng)到今天為止,大致可以分為三個(gè)階段:兩性平等、兩性平權(quán)和兩性同格。早期的女性主義者與最初的女權(quán)運(yùn)動(dòng)通常被稱(chēng)為“第一波女性主義”(the first-wave),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義被稱(chēng)為“第二波女性主義”(the second-wave)。也有第三波女性主義(the third-wave),三個(gè)“波”之所以如此稱(chēng)呼,是因?yàn)榫拖窈@税悖粋€(gè)接一個(gè)永不間斷,后來(lái)者運(yùn)用了前行者的貢獻(xiàn)與資源。
女權(quán)主義在輿論空間
春晚事件
春晚再一次讓女權(quán)主義以憤怒的姿態(tài)進(jìn)入了公眾視野。
在其樂(lè)融融的春節(jié)期間,一群人對(duì)“性別歧視”的討伐,掀起了公共空間里的論戰(zhàn)。北京的婦女傳媒監(jiān)測(cè)網(wǎng)絡(luò)“女權(quán)之聲”歷數(shù)了春晚歧視的種種罪名,發(fā)起了“抵制毒春晚”的聯(lián)名信,得到了眾多響應(yīng)。
然而與此同時(shí),“玻璃心”、“過(guò)敏”、“偏激”,這些標(biāo)簽又被扣在了女權(quán)主義者的頭上,似乎很多本對(duì)春晚毫無(wú)好感的人們,也因?qū)?ldquo;女權(quán)”的抵觸,而站在了春晚那一邊——打起了“捍衛(wèi)春晚言論自由”的旗號(hào)。
周?chē)?guó)平“直男癌”事件
還未淡出公眾視野的周?chē)?guó)平“直男癌”事件,也曾是女權(quán)炮火連天的戰(zhàn)場(chǎng)。
兩個(gè)月前,周?chē)?guó)平發(fā)表微博寫(xiě)道,“一個(gè)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論她在癡情地戀愛(ài),在愉快地操持家務(wù),在全神貫注地哺育嬰兒,都無(wú)往而不美”。周?chē)?guó)平被指責(zé)為自戀的男性知識(shí)分子,給女性灌雞湯的“隱性”壓迫者。
“直男癌”這個(gè)詞語(yǔ)的出現(xiàn),第一次讓女性有了對(duì)男權(quán)價(jià)值的反擊力,網(wǎng)絡(luò)上也隨之伴有大批的女性團(tuán)結(jié)在了一起,反對(duì)男權(quán)價(jià)值的洗腦。但關(guān)于“直男癌”的討論和診斷還未退去,網(wǎng)絡(luò)上馬上又興起了一個(gè)新的流行詞——“女權(quán)婊”。
“武媚娘剪胸”事件
去年年底湖南衛(wèi)視的熱播劇《武媚娘傳奇》突然被廣電總局叫停“剪胸”的事件,先是掀起了男性為主體的輿論風(fēng)波。事件被大量網(wǎng)友吐槽,一篇名為《只許官員玩奶,不許百姓看胸》的帖子在微信上廣為傳播。
在男性用“看大胸”的欲望向公權(quán)力抗辯時(shí),在極權(quán)和男權(quán)兩相爭(zhēng)奪對(duì)女性身體的話語(yǔ)權(quán)時(shí),女權(quán)主義者們打破了這個(gè)格局,展開(kāi)了女性對(duì)女性身體話語(yǔ)的爭(zhēng)奪。呂頻、李思磐和艾曉明紛紛發(fā)出了聲音,雖然這些聲音內(nèi)部也有分歧,卻也掀起了對(duì)“男性凝視”和對(duì)“消費(fèi)女性身體”的集體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