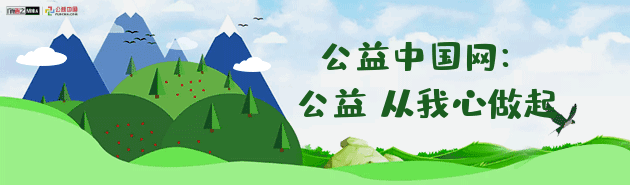一部《長安三萬里》,見識了大唐盛極而衰三十多年。
四十八首璀璨唐詩,講述了時代筆下訴說不完的浪漫與遺憾。
故事的開頭,安史之亂爆發,吐蕃兵臨云天城,時任節度使的高適退守瀘水關向監軍程公公回憶起他與李白波瀾壯闊的一生。
我們也跟隨這段回憶,悉數著那些墜入時光銀河的遺憾。
01
洞庭湖畔,青年時期的高適與李白初次相逢。
他們一個是沉穩奮進的世間人,一個是超脫不羈的謫仙人。
看似性格截然不同的倆人,骨子里的本性卻是出奇一致。
他們有心懷天下的抱負,也有對人間的不盡悲憫。
那年,他們意氣風發。
一個要直趨長安,叩天子門,一個要江夏干謁,施展才華。
他們相信在這榮耀的大唐盛世,憑借自身的才能,就可脫穎而出,就能建立不世功業。
于是,在李白“你我值此盛世,當為大鵬”豪言中,兩人向著理想踏馬而去。
可很快,現實就給了這份理想當頭一棒。
因為出身問題,李白江夏干謁以失敗告終。
此時的李白并不明白,不是所有的大門都會為才華敞開。
就如高適回憶中感慨:哪里有什么科考的捷徑,所謂的干謁,又豈是為寒門所準備。
不甘無奈的他只好帶高適到黃鶴樓喝酒遣懷,正想為此樓題詩時,卻被崔顥筆下的《黃鶴樓》擊潰。
雙重挫敗之下,李白也陷入莫大失意中。
但他的失意,在旁人看來總是那么叫人捉摸不透。
前一秒憤憤不平,后一秒又極盡豁達。
在與高適分別時,他說:“你心中的一團錦繡,終有脫口而出的一日。”
此后,自己又繼續游歷干謁,一次次嘗試,一次次碰壁。
時間更迭中,李白也從也從曾經的俊朗青年走到了中年。
仕途無望,作詩的名氣卻大了起來。
四十二歲那年,他的詩詞傳到唐玄宗的耳中。
玄宗欣賞李白的才華,便一紙詔書將他召進了宮。
以為自己終于守得云開見月明,于是大筆一揮,寫下: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可回頭卻發現,在這朝堂之上,自己的才華不過是供別人取樂。
不得志的日子里,他只能將自己喝得爛醉,或許只有在醉酒作詩的狀態里,他才能活成那個飄逸賽神仙的李白。
這種醉生夢死的日子倒也不長,短短一年過后,李白被賜金放還。
他又繼續游走在山河間,又做回了原本的蓬蒿人。
02
直言要叩天子門的高適,在那年與李白告別后,也曾帶著雄心壯志趕赴長安。
卻發現,在繁華盛大的長安城,卻找不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好在岐王愛才,給了高適一個能被公主舉薦的機會,王維也在其中。
于是宴會上,高適展示出一套出神入化的高家槍法。
可只知賞樂的權貴,又哪懂這上陣殺敵的槍法。
那晚,王維成功被薦,高適抱憾退場,
不知去往何方的高適,回到了老家梁園。
每日種田席地、練功讀詩......就這樣他也從一個健碩青年走到了中年。
但看似平淡如水的日子并沒淹沒他年少時心中那團烈火。
他依然盼望著征戰疆場、建功報國。
于是在收到李白來信,表示能在長安為自己助一臂之力時,他火速趕往了長安。
奈何那時的李白,自己也無法在朝堂施展抱負,更別說幫助別人。
所以,李白沒有實現信中的承諾。
高適又再次回到了梁園。
終于在公元752年,高適迎來了屬于他的機會——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請他入幕府任掌書記。
機會喜憂參半。
喜的是這份差事能讓高適進入他日思夜想的軍隊;憂的是雖然身在軍隊,但掌書記屬于文職,不能圓上陣殺敵之夢。
但他還是果斷前往,在軍隊中他一身文官打扮,放下高家槍,拿起記事筆。
日子一天天過去,在軍營里,他送走了中年,迎來五旬。
也正是半百之際,他被封侯拜相,年少時的夢想這一刻終于實現。
可一看,人已半百;
再看,山河破碎。
03
而少年杜甫的出現,則直接讓人陷入破防。
哪有人生來滄桑,杜甫也曾是個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孩童啊。
因為出身名門,影片里,他是隨意出入岐王府的公子哥。
那會兒的他,不諳世事,眼睛里滿是純真與自信。
后來,少年慢慢長成青年,夢想著在廣闊天地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
可行路難啊,這個節骨眼上杜甫家境已趨向衰落,他的科舉也是連連受挫。
在父親離世后,從沒操持過生計的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
為了謀生,他只得接受現實,做了個曾經無論如何都瞧不上的“芝麻小官”。
后來安史之亂爆發,民生凋敝,滿目瘡痍。
他帶著家人,加入逃難的人群,寫下: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逃難到成都后,杜甫在朋友的幫助下搭建了一個的茅草房,算是暫時安頓下來。
就這樣,后半生無盡的苦難,讓曾經自信瀟灑的少年變得滿面風霜。
盛唐的故事里,那些年輕的身影總懷揣著遠大期許,他們要出將入相、封狼居胥。
可盛唐的故事里,沒有圓滿的人生,李白、高適、杜甫、王維、岑參、王昌齡、賀知章......
太多懷才不遇的文人、報國無門的女子,他們在時代的征程中,走不出,回不去。
但遺憾的人生里,他們卻向我們講述一個關于不朽的故事。
李白干謁被拒后,他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瀟灑落筆,寫下“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后揚長而去。
年老時,因誤追隨永王叛亂,好不容易脫離死罪的李白被發配夜郎,中途遇大赦,李白乘舟返回的路上,他沒有悲嘆人生不公、命運玩弄。
反而寫下了《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大器晚成的高適,面對戰爭,他已不再是當年身強力壯的小伙兒,卻依然以暮年之軀護衛家國。
還是會說出這句:“只要詩在,長安,就會在。”
目睹亂世之下百姓流離失所的杜甫,心境發生翻天覆地改變。
他不再執著于自己的遺憾苦難,而是將筆觸伸向黎民疾苦,在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寫下了諸多反映百姓疾苦的詩篇。
誰又能想到這個在岐王府無憂無慮的頑皮孩童,會在若干年后,寫下“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
命運給了他們種種苦難,致使他們的人生有了種種不可彌補的遺憾。
他們會失意,會垂頭、也會借酒消愁,但當再次回眸,他們已然接受這萬般不公。
在旁觀者看來,他們彷佛是將這些苦難遺憾,視作過眼云煙。
他們曾自比大鵬,其實他們就是大鵬。
他們扶搖直上,穿越千年歷史而來,告訴我們:
每個時代都有遺憾,每個生命都有憾事。
而這些憾事,不過人生常態。
我們能做的不是自此潦倒、消極待日,而是握手言和。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漫長的人生里,總有遺憾不能避免,既然不能不避免,不如一門心思過好當下。
千年前,他們向往長安、奔赴長安,在那里,他們有太多遺憾,但也有了流傳千古的光輝。
千年后,無數當代青年心中也都有一座長安城,也許距離它的路程比三萬里還要遙遠。
但只要出發,只要走好當下,那便是命運予我們最好的安排。
文章轉載自公益中國網:http://www.gzjgpet.cn/news/show.php?itemid=97535
圖片源自網絡,若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