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兒童文學之“大”
2009年07月22日 17:11 來源:中華讀書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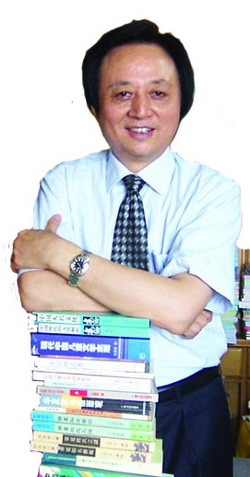
世人皆以為兒童文學“小”,殊不知其“大”。其“大”不僅因為接受者群體之“大”,接受者群體作為人類未來之“大”,更在于其哲學根基之“大”。
王泉根:兒童文學之"大"
王泉根在中國兒童文學學術領域所做出的貢獻眾所周知,其堅執“問題意識、原創品格、中國話語”的學術理念亦為學界所稱道。王泉根著書、編書上千萬字,然其自選集《王泉根論兒童文學》雖只收錄36篇文章(55萬字),卻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兒童文學學術論著。單是第二部分(共14篇),連綴起來即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史。從兒童文學發生的邏輯起點說起(《論兒童的發現與兒童文學的發現》),進而分階段梳理——論“中國兒童文學的傳統印記”、論“五四”兒童文學、論文學研究會的“兒童文學運動”,一路梳理到新世紀兒童文學研究,再做俯瞰式的整體觀照——論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三次轉型與五代作家、論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經驗與人文價值、論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外來影響與對外交流,史論結合、縱橫對照,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脈絡、成敗得失及內在演變機制即全景式地展現在眼前。前加基礎理論研究及學科建設研究(12篇),后有作家作品研究(10篇),如此宏闊而脈絡清晰的格局,充分體現了王泉根構建開創性理論體系的學術理想、學術潛質和學術實績。王泉根的學術形象也因此變得明朗清晰。
兒童文學是20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界最重要的收獲。無論創作,無論翻譯,無論理論研究,無論學科建設,都以積極的態勢在行進、在建構。兒童文學作為一種詩性力量,在一個消解意義的時代里顯示了“文學”存在的理由和終極價值。
一種文學形態、一個學科的興起、發展和成熟以及它春風化雨的社會效應,包含著極其復雜的過程。兒童文學尤其如此。在一個對兒童文學存在根深蒂固的觀念偏見的國度,在一個兒童文學長期無法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度,有膽識、有魄力的兒童文學學人的出現及成熟的兒童文學理論系統的建構就具有至為重要的意義。歷史將記下新時期成長并成熟起來的一代兒童文學學人的名字。作為中國第一批兒童文學碩士、第一位兒童文學博士生導師,王泉根的兒童文學事業是從清理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運動開始的,自此,史料的梳理、考訂與辨析成為他從未間斷的基礎性學術工作,這樣的起點賦予了他日后敏銳的史家眼光和高屋建瓴的學術判斷力。當歷史的因緣際會把他與北京師范大學這一有百年學術根基和豐富學術資源的兒童文學發展基地聯系在一起時,他的學術定位就起了巨大的變化。他自覺到一個“兒童文學建設者”、一個“兒童文學學科帶頭人”的學術身份與學術使命。這種學術擔當意識以理論形態在這本書里得到全方位的體現,并直接促成了王泉根的充滿現實關懷、充滿問題意識、融貫學術理想、注重體系建構的學術風格,自覺的學術身份體認亦使他時時觸及兒童文學的詩性本體特征,進而激發出無與倫比的學術熱忱與學術智慧,并最終體現為“知行合一”的學術品格與學術精神。這是王泉根以及他的兒童文學事業最使人感動的地方,讀懂這一點,或可從更深的層次上理解他的學術格局與學術胸襟,亦從更深的層次上理解兒童文學的價值與意義。
基礎理論體現的是一個專業學人對于自己學科的本體論理解,是為自身學科的存在尋找哲學的根基。論著的開篇即《論兒童文學的基本美學特征》,接著是《論兒童文學在文學大系統中的位置》,這樣的安排,我以為體現的正是兒童文學的大氣象和大胸襟。世人皆以為兒童文學“小”,殊不知其“大”。其“大”不僅因為接受者群體之“大”,接受者群體作為人類未來之“大”,更在于其哲學根基之“大”。王泉根將“以善為美”作為兒童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與基本美學特征,是“冒險”的學術表達,卻也是能充分體現他的理論創見和理論取向的學術表達。
在哲學的范疇里,真、善、美是統一體,真實的東西,就是美與善的東西;美的東西也就是善的東西。然而,三者終究是三個概念,可見概念間自有區別。我相信王泉根使用“以真為美”和“以善為美”作為審美的兩個幅向時,一定經過反復的思量,并對概念之間的意義縫隙有充分的覺察。然而,概念的內涵確定取決于具體語境的限定,正是具體語境使得意義界定成為可能。他將工業文明時代的人類理性思維、科學主義、功利主義與人類童年時期的感性思維、整體觀念作為相對立的一組前提概念提了出來,指出工業文明使人類世界最終形成成人世界與兒童世界的兩極客觀分離。那么,人類發現兒童、尊重兒童,即人類終于有能力來“重新認識自己的童年”,重新“認識生命個體的童年世界的存在意義與其在精神生命上的特殊需求”。為使人類擺脫科學主義、工具理性的桎梏,真正將人視為“目的”而非“手段”,則人應在理性上尊重兒童的思維特征和心理特征,并通過文學審美之途徑“來充分地、妥帖地保護和珍視兒童精神生命中本性之美,使童心努力地不為惡俗所異化”,因此主張兒童文學的題材內容應有所規避,從而使少年兒童在早年獲得對抗異化的信心和能力。這一理論判斷和理論標尺既是倫理學意義(康德的“人是目的”)上的判斷,也是審美意義(兒童的天真是人類文學精神的最高境界)上的判斷,更是實踐意義(實現人類社會對下一代的文化期待、為人類構筑良好的人性基礎)上的判斷。
這是一種對于文學的詩性價值的肯定,是王泉根對于“兒童文學”終極意義的哲學回答。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理解了兒童文學之“大”,也就理解了王泉根的學術熱忱和學術信心,進而理解了王泉根何以說——“如果選擇兒童文學是人生的幸福選擇,那么選擇兒童文學研究則是使生命永葆蔥綠的智慧選擇”。而王泉根在學科建設上有目共睹的業績——包括對學科性質和學科建設的理論思考,實踐中對學科學位點的申報及方向設置,培養學術后起人,鼓勵作家的探索與原創,參與圖書策劃支持出版,聯手中小學語文教育,主持、參與各類學術交流和研討,積極與國際、與海內外交流,編撰教材等等。這種知行合一、身體力行、“少說空話、多干實事”的精神,這種時刻以對專業的忠誠、敏感和智慧去感染人的熱忱,共同構成了王泉根的學術氣象和學術襟懷。
李紅葉 王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