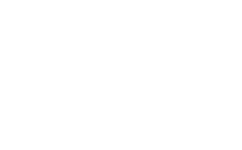一、伏爾泰開創先例
關于這個主題,我先介紹一段歷史。1755年11月5日,葡萄牙的里斯本發生地震;成千上萬的人在災難中喪生。消息傳到法國,著名哲學家伏爾泰迅速做出回應,寫了《里斯本災難詩》:
“那些口誦“一切都好”的誤入歧途的哲學家們,來這里吧,穿越、沉思這些可怕的廢墟,這些殘骸,這些尸體,這些凄涼的灰燼;女人、孩子,層層枕籍于碎石之下,身首異處;千萬不幸的人們被大地吞噬,鮮血淋漓,四分五裂,生命依然悸動;人們被埋于自家屋頂下面,在無助、恐怖、痛苦中死去。”
伏爾泰進一步闡明,這場災難中的什么因素在哲學上無法接受:
“這些孩子犯下了什么樣的罪孽、什么樣的過錯,以至于在母親的胸脯上壓碎、流血?里斯本難道不是與耽于淫樂的倫敦、巴黎同樣墮落同樣腐敗嗎?究竟是為什么,里斯本招致毀滅,我們卻在巴黎縱情歌舞? ”
為什么要提到這段歷史呢?根據當代一位學者伊娃· 伊洛茲(Eva Illouz)的觀點,伏爾泰在這個事情中開創了先例,這是哲學家第一次就同時代的、在遠方發生的災難直接面向其哲學界同仁與普通公眾發言表態。(參見伊娃· 伊洛茲:“從里斯本災難到奧普拉· 溫弗莉:全球化時代作為身份的苦難”)。
伏爾泰的表態引發了法國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論戰之一,哲學家們就“神意”(Providence)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
在這之前,人們對于苦難抱一種“神正論”的態度。意思是,遭到懲罰者,必然有一種隱秘的罪孽。神意高深莫測,我們只能接受。
除此之外,民間還有一種“感傷文學”式的態度,即以悲憫情懷和柔腸眼淚接受苦難,甚至把苦難看作是天命裁判而膜拜。
伏爾泰的立場是完全相反的,他要求,苦難必須能夠理解。即便苦難是上帝對于罪孽的懲罰,也必須被人類理解,否則不可接受。
所以他問,天真無辜的孩子們能有什么罪孽?所以他問,如果里斯本這個城市因為耽于淫亂而遭受天譴,那么倫敦和巴黎不也一樣嗎?為什么里斯本遭受滅頂之災,而我們卻可以在巴黎縱情聲色?這樣一來,伏爾泰代表那個時代的思想者,第一次對“神意”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提出了強烈的質疑。
伏爾泰所開創的這個先例,對于我們今天談論公益傳播,有許多啟發價值。首先,他試圖建立一種遠距的同情和關懷,將遙遠的他人的苦難視為人類共同的苦難。其次,這種普遍的同情中,包含了道德上的責任觀念和反省態度。也就是說,面對他人的苦難時,我們需要反思自身。再次,人類的普遍而共通的道德情感,表明我們不需要依賴神意,也可以有一種人類整體的道德一致性的空間。
在伏爾泰的時代,這個空間意味著一個世俗化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全球公共領域,或全球公民社會。
二、信息過載之下的道德冷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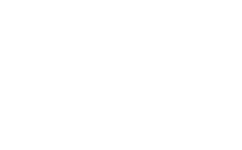
可見,通過對苦難的詮釋和傳播,伏爾泰試圖建立一種獨立的人類自身的身份,并在全球尋求認同。
今天我們身處互聯網時代,網絡的邏輯是扎克伯格所說的“連接所有人”,這就等于實現了伏爾泰的理想。但是,由此而來的一個后果,卻是伏爾泰沒有想到的,這就是普遍的道德冷漠。這是因為蜂擁而來的信息導致信息過載,如果對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出道德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反應,個人就會負擔太重,出現所謂審美疲勞。
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提出過相反的問題。如果每一個人的個體生涯都對整個世界開放,如果我們總是需要在一種遠距的道德關系中做出反應,那么就要想,在街角喝一杯咖啡,會不會成為壓榨南非咖啡種植園工人的同謀?
美國消費者曾發動過抗議運動:當你穿某個品牌的衣服時,你要想它是不是血汗工廠里的工人制造出來的。這會把你每一次個人的消費都跟遙遠他人的苦難勾連起來,并要求你承擔道德的拷問。可是這樣一來,問題會無窮無盡,你用蘋果手機嗎?你穿皮草嗎?你吃狗肉嗎?……
在此情形下,人們會下意識地拒絕做出反應,用忽略信息、用冷漠態度來保護自己。
信息化、全球化、網絡化的世界中,如何重新塑造人的關心和人的情感?人會在身份認同上存在兩方面搖擺:一方面,借助技術便利知道更多,因此更容易發生道德的憤慨;另一方面,當你一旦引入對自己反思時,會感覺到負擔太重。沒有人能夠承受天天在想遙遠他人的苦難,因此基本心理保護就是冷漠,我不看也不想,我不可能去承擔這么大的責任,我不能承擔這么多東西。
在這里,道德問題轉化為心理問題。個體必須持久挺立,做出反應,因此承受力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許這可以解釋很多過去不能解釋的事情。好好的一位學生,突然投毒害死了同寢室的舍友。大家第一反應就是,何以道德冷漠到這個程度?接著會想,他可能心理上出現問題了。
三、冰桶挑戰的創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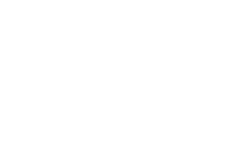
對于媒體來說,講述和報道遙遠的、他人的苦難,呼喚普遍的反思和同情,這種伏爾泰式的做法,現在越來越難。當然這種做法永遠都有其重要性,但是,至少是效果越來越不確定了。
正在出現的,是一種苦難傳播方式的轉變。非常簡化地說,原來是聽別人“再現”一種苦難,例如伏爾泰向法國公眾傳播和解釋發生在里斯本的事情;現在變成自己“直接呈現”自身的苦難。“直接呈現”也是一種呼喚,呼喚同樣境遇的人走出來,各自呈現。
典型的做法是美國一些知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做脫口秀節目,直接講自己的隱私,例如多年來隱藏于內心的對于父母長輩的怨恨,年少時曾經被性侵,等等。節目招來大批的自愿參與的談話嘉賓,講出各種難以啟齒的內心痛苦,吸引了大批觀眾日日追隨,一同唏噓。
在這里,再現他人變成了呈現自己,對外界反應的需要變成了自己想參與的自愿,道德憤慨變成了“終于說出來”之后的道德減壓。
如果能夠理解這些,就能夠理解“冰桶挑戰”。冰桶挑戰是通過網絡平臺而傳播的,它的典型特征是傳播過程像水一樣流動,沒有固定形狀。但是,基本的要素還是清晰可辨的。
第一,它傳播苦難,是他人的、可能遙遠的苦難。與大災害相比,這是一種“低度苦難”。
第二,它提供了一種簡單的代入體驗的方式,這種方式有很強的游戲感,又有隨機創作的空間,于是吸引了很多人參與。
第三,整個參與過程產生出社交和快樂,這里確實沒有什么道德憤慨w。
從中再次看到,網絡傳播具有非線性、碎片化的特點,它消解宏大敘事。不過也正因為這樣,它反而能夠帶來大規模的自愿參與。這里沒有冷漠,卻有很多熱情,同時有非常可觀的籌款效果,因此我們還是需要認真思考其中的道理。
很多人認為這類事件是有推手推出來的,我也相信是這樣,實際上,還有很多名人明星參與其中,他們也有推動的意圖。不過在網絡上,想推的人很多,推成的不多。所以不是你想推,想推就能推的。
關鍵在于,大多數參與者是自愿的,并沒有一個傳統的組織動員的過程。這里表現出一種新的主體性。人除了是理性人、經濟人、勞作人等等之外,更根本的,可能是荷蘭學者赫伊津哈說的“游戲人”。人們自由平等地創作游戲,參與游戲,其中的激勵因素不是功利,而是參與感、快樂與勝利者的榮耀。
四、自我呈現的時代
總的來說,由于有了網絡自媒體,傳播領域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自我呈現、直接呈現。主要承擔“再現”功能的傳統媒體就衰落了。
當然這是從比較意義上說的,衰落不等于不存在,只是它不會再占據中心位置,而變成傳播方式之一,變成表現方式之一。當我們討論公益傳播、苦難傳播的時候,要注意這個基本面的變化。
不少人擔心,像冰桶挑戰這種傳播方式,會使公益慈善變得輕浮,作秀成分太重。我自己也把冰桶挑戰稱之為“輕慈善”,與傳統的“重慈善”相區別。因為它不依賴宏大敘事,與那些艱苦、沉重、瑣細的實務環節脫嵌開來了。
如何看待這樣一種情況呢,確實需要討論。但是我們還是要面對這個變化,自己要參與進去。同時還要看到,在參與和自我呈現這個維度上,各種傳播現象其實很復雜。我歸納了幾種,當然還是非常簡單化的。
■溫弗莉脫口秀(低度苦難與隱私)
■冰桶挑戰(低度苦難與快樂關懷)
■自殺直播(高度苦難、生命困惑、個體的)
■占領運動(高度苦難、身份困惑、社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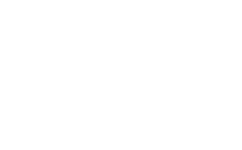
溫弗莉脫口秀
關于占領運動,可以多說幾句。那么多人跑到街頭去睡覺,構成一種大型表演,它也是一種自愿參與的、直接呈現的苦難傳播。
他們可能有一種痛苦,一種困惑,我是誰呢,我的生活在哪里呢?既然沒有一種話語能夠“再現”他們的苦難,那他們就自己“呈現”自己的苦難。這種呈現是多種多樣的,事實上我們看到,其中也有很強的參與游戲的成分。
現在還很難對所有這些變化提供全面的解釋。我只能簡單地總結說,如果希望公眾參與,那么,構建一種游戲場景和互動平臺非常重要。不僅如此,人們越來越尋求自我闡述和直接呈現,而不依賴于讓別人來“再現”自己的事情。這當中,有輕喜劇,如冰桶挑戰。也有極為沉重的悲劇,如自殺直播。
我們要發展公益傳播,需要對這些事情有更多的思考。更需要的是創造性地發展出直接行動/直接呈現的傳播方式。
講者介紹
郭巍青
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壹起社會研究中心監事
此文為由壹基金、壹起社會研究中心主辦的“2014第三屆全國公益•媒體年度交流會”上的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