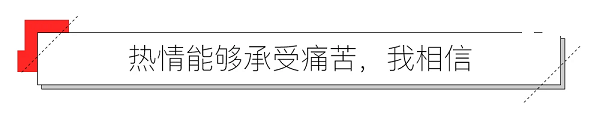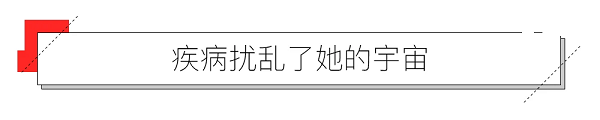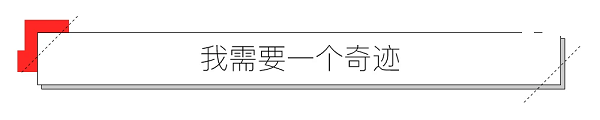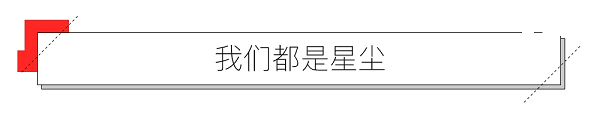2019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拉遠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給海外留學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如今三年過去了,世界還在飽受疫情、甚至戰火的分割,而那些依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留學生們,又在面臨怎樣的考驗呢?
系列紀錄片《一次遠行》通過16個月的跨國拍攝,記錄了5位中國青年人的留學生活。他們身處美國蒙大拿、以色列特拉維夫、美國紐約、法國巴黎、德國萊比錫......疫情之下,他們如何用熱忱化解身處異國的孤獨?又如何在困境中尋找光亮?
故事的第一位主角,是一個夢想成為科學家的女孩子,她叫周倩儀。
“默克爾是我們師姐哦,她也是萊比錫大學畢業的,學物理的。”
在前往醫院的路上,29歲的周倩儀跟媽媽驕傲地講述著自己的學業與理想。
與很少穿裙子上街的德國女孩一樣,周倩儀更喜歡牛仔褲和馬丁靴。但跟很多女孩不一樣的是,她熱愛星際飛船、天文與物理學,并夢想著有一天,能成為一位女科學家。
她想親自來驗證,女孩子對科學也是有興趣和能力的。
“我本身在國內是學經濟的,那時候大家都說女孩子要學經濟,就跟風去學了。可我對經濟一點興趣也沒有,我當時就真的開始想了,我現在到底是在干什么,我到底以后要干什么。我還是想做物理多一點。”
2017年經濟學畢業后,倩儀辭掉工作前往德國,來到萊比錫大學重讀本科,并順利申到了她心愛的物理學系。
倩儀一頭扎進了屬于她的宇宙。“我對自己的目標非常清晰,天天去圖書館,泡個6個小時、8個小時,但我很喜歡那樣子的學習。”
有一些科學家,他們一輩子就做一個項目,幾十年就研究一個東西。在倩儀看來,這是一件無比偉大的事。她崇拜這件事,也樂于沉浸于此——在看似枯燥的學術研究里,長期鉆研,探尋秩序、理性與科學的快樂。
“我相信,熱情是能夠用來承受痛苦的。”
倩儀不喜歡穿裙子,短發更讓她看起來有一股英氣。
2018年,她遇到了男友Romel,這位來自厄瓜多爾的高個子男同學,在萊比錫大學主修音樂制作。憑著對爵士樂的熱愛,倩儀與Romel走到了一起。業余時光里,愛音樂的德國朋友們聚在一起,擺弄樂器、唱唱歌,這點亮了倩儀的留學生活。
29歲的女孩開始漸漸完善自己的宇宙:熱愛的物理學、相伴的友人,清晰的自我認知。生活以這樣的姿態持續推進著,穩定且充滿動力。以至于在身體出現異樣時,她并沒有很在意。

倩儀在和朋友們小聚,倩儀唱歌,男朋友為她彈吉他伴奏。
開始只是胃痛,持續不斷的胃痛。
周倩儀并未多想,照舊生活和學習,實在疼痛難耐時,就吃點藥壓制。
直到2019年11月的某一周,她開始頻繁地嘔吐,肚子也持續腫脹,直到腫得像個孕婦,她去做了全面的胃部檢查。
德國醫院確診這是胃癌晚期,周倩儀覺得有些荒誕。
“怎么會碰上癌癥呢?我注定是要做成些什么的,一些讓我生命變得獨特的事,一些我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我都還沒有完成,怎么會碰上癌癥呢?”
對于人類的身體探索,同樣也是科學探索的一種,可周倩儀也沒辦法明白。

倩儀在醫院中抽血準備復查。
疾病擾亂了她的宇宙。一時間,數字對倩儀的意義產生了變化,從追夢工具變成了坐落在病歷上的指標。她不得不把生活的重心從學習上一點點地抽離出來。
但她的想法是:或許并沒有那么嚴重,不如堅持一下,總會好起來的。自己還很年輕,日子怎么會過不下去?
事情并沒有按照周婧儀預想的方向發展。
“2019年確診的時候,第一線化療的效果還好,等到了2020年12月份的時候,情況突然間變得很糟糕。在盆骨卵巢的一個腫瘤現在這么大個,然后另外肝臟旁邊,還有一個核桃大小的腫瘤,除了這些以外我的腹膜上面都是那種小小的,小芝麻一樣的病灶。”
周倩儀說這些的時候,面帶倦色地斜仰在床上,表情非常冷靜。過去一年的化療讓她變得身形清瘦,長發也被剪成了圓寸。

倩儀斜躺在床上,此時她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
確診后,倩儀選擇留在了德國,一邊接受治療,一邊寫畢業論文。可幾個月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全面爆發。一時間,各國防疫政策相繼出臺、國際航班頻頻熔斷,回家路變得漫長與艱辛。
為什么當時不選擇回國呢?
“后悔,當然后悔沒有早點回去。但那個時候就是覺得,看看能不能再堅持一下,把論文也給寫了,把學業完成。我的家里,就我和我弟上過大學。就想有點兒成就,上完學回去,多有面子,也給家里增光。看,我家里出了個物理學家。"
提到“家”,一貫保持克制的倩儀強抿著嘴,眼淚忍不住流下來。
“可是現在不想這些了,現在如果回家就好了,回家就好了。”
為了能夠更方便地照顧女兒,倩儀媽媽飛往了德國。可在一次復診之后,醫生給出了答復,無法安排手術治療,“已經沒什么可能了”。
但倩儀需要一個奇跡。
她開始努力地變成一個“專業的”病人——不只是被動地接受醫治,而是自己查閱更多的醫學文獻,分析自己的病情,充分了解她現階段能夠擁有的所有的選擇。
她了解到,亞洲是胃癌的高發地,相較德國,國內的醫院可能會有更豐富的經驗。于是,她拜托了上海的同學幫忙尋找國內可行的治療方案。哪怕還有一線機會,她也想盡力拼一把去爭取手術,直到上海的一家醫院給出了一個較為樂觀的答復。
回國吧,人終究是要回到家里去的。

即將啟程回國的倩儀,享受著最后與朋友相處的時光。
敲定航班,做核酸、驗血清、拿綠碼、防疫碼..……回國的手續準備就緒,倩儀和媽媽松了一口氣。
她開始整理自己在德國兩年的行李:珍藏的Falcon9T恤、雜物和重要的課業教材。“這是數學,這是那個經典物理,這本電磁學我是看了很多很多遍的。”倩儀把它們整齊地碼進行李中。

倩儀在向我們展示她的Falcon9 T恤。
德國友人為倩儀補辦了29歲生日,他們一起在燭光下歡笑、歌唱,再一次暢聊天文學與物理。
男友Romel因為簽證問題無法來到中國,但是依舊選擇陪倩儀和媽媽從萊比錫飛往法蘭克福。一路上,Romel推著行李,低頭走在倩儀身邊默不作聲,倩儀在一旁哼著歌,兩人始終不太敢看對方,直到登機口分別時,緊緊相擁。
我們還會見面嗎?倩儀沒有答案。
但她不得不地暫時告別德國的一切,暫停自己熱烈追逐的科學夢想。
踏上故土的一刻,倩儀有些恍惚。
癌癥和疫情于自己、于世界都變得如此不可知,好在隔離的十四天里一切平安順利。
在確診十五個月后,倩儀爸爸第一次見到女兒。因為化療,倩儀的樣子變了很多,“你怎么這么瘦了?”爸爸語氣溫柔地問,倩儀沒有正面回答。
可是,希望還是落空了。
上海那家醫院的醫生只給出了很模糊的回答,倩儀不想再浪費時間,她決定開始自己找醫生。可另一邊,倩儀爸爸卻一直希望女兒能跟他回廣州。在他看來,廣東老家有更合適的就醫機會,在上海這樣一個大都市,沒有熟悉的醫生,爸爸對女兒的健康沒有一點把握。
“在國外我真是沒辦法,到了國內不管多少錢好吧,明天早上或者什么時候我們聯系。”午飯之后,倩儀爸爸獨自走到樓外抽煙,并給廣州的醫生朋友打起了電話。
“其實我不是想找什么最好的醫生。”面對爸爸提出的找最好的醫生的說法,倩儀有些漠然。“我就是想找對我比較有信心的醫生,比較積極一點。”

一家人從上海的醫院出來,天已經黑了,倩儀爸爸的背影顯得有些滄桑。
上海的春天落著雨,倩儀帶上相機獨自出了門,她與舊友坐在咖啡廳里聊天,重拾一些讀書時的回憶。
“我還記得小時候班上的男孩子欺負我,罵我男人婆,然后又把我推到地板上,然后頭還撞到凳子,是一個“死”胖子。我就希望成為一個非常堅強的女生,不要成為被欺負的那一個。”倩儀和朋友說著,笑著。
她逐漸地松弛下來,這樣的一場出逃讓她從家人關切的目光中暫時抽離,也獲得了一些新鮮的養分。

倩儀回國后,與友人暢談。
幾天后,倩儀與父母一起回到了廣東老家。
久別的故鄉還是那樣溫馨和熟悉:弟弟做專屬司機,帶著倩儀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和闊別已久的朋友們聚餐、喝奶茶、聽livehouse、做美甲;拿著相機去掃街,隨手拍就是鮮活動人的日常。
在德國時,男友總是拿著吉他為倩儀伴奏,而回到家鄉,她在朋友的陪伴下登臺演唱,不時出現的疼痛總會提醒著她,生活需要她足夠勇敢地繼續下去。

倩儀回國后,在舞臺上唱起了自己心愛的爵士樂。
治療也在繼續。
廣州的醫生會診完,得出結論:腫瘤越來越大,已經嚴重壓迫了身體神經,影響到了倩儀的日常生活。但腫瘤過大,化療藥物的作用也不再明顯,如果做手術也無法切除原病灶,僅僅能改善部分生活質量。
倩儀陷入了矛盾......
從德國到上海,再到廣州,這個如星塵般炫目的女孩,最終會走向怎樣的征途?面對似乎無法抵御的苦痛,她又該如何找回屬于自己的光亮呢?

倩儀在病痛與奔波之下,顯得格外疲憊。
倩儀曾經囑托弟弟,在她走之后,如果天文學和物理學要是有了什么新的發現,可一定要告訴她。
“有一句話是,我們都是星塵,其實星星死了都會爆炸變成下一代星系的原材料,這是很浪漫的一個說法。”
周倩儀,一個熱愛星際飛船、天文和物理學的女孩子,一個想要成為科學家的女孩子。
她注定會把生命綻放,如同一顆璀璨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