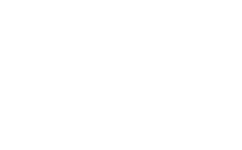
王兵沒有想到一個運(yùn)動不僅能讓人下崗、失去工作和沒有生氣,還能夠讓人吃人、讓人吃別人的嘔吐物,甚至讓人今夜還在但明早便成為被被子裹著扔到荒地的死尸。
“和空置而巨大的廠房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共鳴感”
王兵拍攝紀(jì)錄片的最初原因,和他最有名的作品《鐵西區(qū)》所表達(dá)出來的情緒一樣,來源對未來的彷徨。在拍攝紀(jì)錄片之前,王兵還未發(fā)現(xiàn)對未來的彷徨其實(shí)來源于對歷史的無知,他后來拍攝的一系列紀(jì)錄片作品,都在試圖尋找到暗處的歷史,并以此來揭開無人發(fā)現(xiàn)的傷疤,讓痛感引導(dǎo)現(xiàn)實(shí)。
王兵出生在西安的農(nóng)村,出生的時候,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1967年。14歲時,王兵的父親突然去世,14歲的王兵根據(jù)當(dāng)時的政策,無法拒絕的頂替了父親在設(shè)計院的工作,還未成年的他一下子代替父親成為了一家的經(jīng)濟(jì)支柱。身處中國社會最為動蕩年代的王兵,一邊懵懵懂懂的工作,一邊努力給家里寄錢,當(dāng)時他的姐姐正在上大學(xué),急需王兵頂替父親賺來的工資。王兵的兒時經(jīng)歷注定了他不想和歷史發(fā)生關(guān)系都不可能,王兵過早的步入社會,當(dāng)時文革浩劫帶著余波剛剛結(jié)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tuán)被打倒,全黨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上臺,他正運(yùn)籌帷幄的準(zhǔn)備實(shí)行實(shí)行一國兩制、改革開放的政策。
歷史似乎走向了光明正途,王兵也從父親的單位離開,想學(xué)習(xí)自己頗為喜歡的攝影。1991年,24歲的王兵離開父親的單位去沈陽電影學(xué)院攝影系進(jìn)修。在沈陽這個因為歷史原因而成為工業(yè)城市的地方,王兵再次和歷史有了親密接觸。那時正巧是國企體制改革,大批的沈陽工廠工人被清退下崗,一時間工人的鐵飯碗紛紛落地。在沈陽上學(xué)的那段日子,性格孤僻的王兵“和周圍的人都非常不熟悉”。“沈陽又是一個工業(yè)城市,與我過去生活的地方差異比較大。我剛到沈陽的時候,情緒一直比較低落,經(jīng)常去這些工廠和鐵路道口之間拍照片,以此來消磨時間”。王兵當(dāng)時最喜歡去拍照片的地方便是后來讓他揚(yáng)名的鐵西區(qū),鐵西區(qū)是一個因為國企體制改革而逐漸荒廢的工業(yè)園區(qū),王兵對這里空置而巨大的廠房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共鳴感。“這些工業(yè)區(qū)的外部形象給人一種象征性很強(qiáng)的感覺,那種大型工業(yè)的軀體,從過去的大工業(yè)激情當(dāng)中,漸漸變得萎縮和衰弱。當(dāng)你個人站在這其中,不由得使你自己感到自己也是這樣,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
和鐵西區(qū)一樣感到未來渺茫的王兵,1999年從學(xué)校畢業(yè)后,告別了沈陽和荒涼、冷寂的鐵西區(qū),去了北京。在北京,王兵并沒有交上好運(yùn)。他先后擔(dān)任了幾部電影的攝影,但這些工作都是像《變形記》那樣幫朋友的忙。“那時候的劇組并沒有什么細(xì)致、確切的拍攝計劃,所有東西都是很松散的,只是你劇組里缺少一個攝影師,于是朋友找到我。那時做攝影工作是很松散的,并不頻繁,也不快樂”。
在北京待了大概3年多的時間,王兵除了幫朋友的忙,同時也是朋友幫他的忙做了幾次攝影師之外,基本上處于無事可做的狀態(tài)。王兵在人潮洶涌的北京街頭,經(jīng)常感到惆悵不已。他開始懷念一個人在沈陽鐵西區(qū)獨(dú)自拍攝照片的時候,蕭瑟的冬日的鐵西區(qū),幾乎沒有幾個人的巨大廠房、綿延百里卻只偶爾有幾輛火車駛過的陳舊鐵軌以及工廠生活區(qū)內(nèi)那些不知命運(yùn)如何只能渾渾噩噩度日的青年,都反而讓王兵的心里涌起一絲溫暖。那時王兵常常站在鐵西區(qū)的廠房里,一言不發(fā)的看著這個已經(jīng)死去的龐然大物。鐵西區(qū)似乎就是王兵當(dāng)時內(nèi)心世界的映射,它暗合著王兵的境遇和心理狀態(tài)。王兵拿著照相機(jī)拍攝這個巨大的廠房和廠房內(nèi)的人,其實(shí)也是在拍攝自己,拍攝一個體制和一個體制下的人。王兵在北京的夜里輾轉(zhuǎn)反側(cè),“鐵西區(qū)”這三個字讓長時間無所事事的王兵仿佛摸到了人生中的導(dǎo)線,他明白鐵西區(qū)里的故事“才真正是人的故事”。
他決定拿著攝影機(jī)回沈陽拍下這個故事。

《鐵西區(qū)》
“拍攝那些沒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們”
回到沈陽的王兵,身上最值錢的東西就是自己用來拍攝影像的DV。他來到沈陽后立刻就去了鐵西區(qū),鐵西區(qū)的廠房比幾年前更加破敗和落寞,人們臉上的表情已經(jīng)完全被失落和灰暗籠罩。和以前在鐵西區(qū)漫無目的的游走不同,王兵再次來到鐵西區(qū),有目的性的重新轉(zhuǎn)了一下這個面積達(dá)到484平方公里的工業(yè)園區(qū)。
本來想為鐵西區(qū)拍個故事片的想法,在鐵西區(qū)這個突然變得紛繁和沉重的題材下,似乎變得無法實(shí)施。更讓王兵苦惱的是資金的問題,當(dāng)時王兵的口袋里只有幾千塊錢,他沒有錢組建劇組,攝影器材也只有一臺精度并不高的DV。題材和資金的雙重問題,讓王兵為鐵西區(qū)拍攝一部故事片的想法走入了死胡同。如何把單薄的DV和體積龐大的鐵西區(qū)聯(lián)系起來,王兵左想右想,他發(fā)現(xiàn)只有紀(jì)錄片這一種方式能完成。
確定了紀(jì)錄片的拍攝方式,王兵發(fā)現(xiàn)導(dǎo)演和攝影只有自己一個人,而到底究竟紀(jì)錄鐵西區(qū)的什么、如何紀(jì)錄,王兵自己還未最終確定。王兵沒有別的辦法,他只有再次不斷的去鐵西區(qū),希望能尋找到一個思路。王兵和上學(xué)時一樣,每天都會定時出現(xiàn)在鐵西區(qū)內(nèi),這和10幾年前王兵一個人在鐵西區(qū)拍攝照片時的狀況一樣,王兵畫了一個圈又回到了起點(diǎn)上。在鐵西區(qū)內(nèi)游走的王兵,因為性格的原因,并不上去和誰說話攀談,他只是拿著DV在鐵西區(qū)的各個地方像幽靈一樣走來走去。王兵“每天都背著機(jī)器在尋找機(jī)會”,他想發(fā)現(xiàn)一個能讓自己形成拍攝欲望的對象。王兵偶爾拿起DV會拍一些影像素材,但他“從不向居民和工人做任何關(guān)于影片拍攝方面的解釋”,只是站在遠(yuǎn)遠(yuǎn)的地方,拉近鏡頭然后拍攝那些甚至沒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們。
在每天每日穿梭在鐵西區(qū)的生活里,王兵意外的發(fā)現(xiàn)了鐵西區(qū)冰冷廠區(qū)角落的生活區(qū)。這個生活區(qū)名為“艷粉街”,光是名字就充滿了和鐵西區(qū)名稱相互抵抗的媚俗意味。艷粉街住著一群在鐵西區(qū)上班的工人和家屬,那里常年盤踞著一幫十七、八歲的年青人和已經(jīng)進(jìn)入遲暮之年的老人。王兵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一般,兩周的時間一直都在這條街上從東走到西,再從西走到東。在王兵的觀察下,他發(fā)現(xiàn)“這群十七、八歲的年青人,每天無所事事地走在堆滿積雪與垃圾的社區(qū)里,他們的出現(xiàn)為這個社區(qū)沉悶的生活帶來一絲生命的活力,他們是代表著這個區(qū)域最有生命活力的群體,對他們生活現(xiàn)實(shí)的表達(dá),是最具有象征意義的,我和他們在一起,也使我不斷地在思考我自己過去的生活。”
“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么”
從艷粉街找到突破口的王兵,決定把《鐵西區(qū)》這個還未形成清晰形象的故事徹底搞清楚。王兵想要展現(xiàn)的,是鐵西區(qū)這個工業(yè)時代理想化破滅后的人走茶涼,以及在這樣看似沒有希望的土地上生存著的人們的苦樂酸甜。王兵自己擬定了一份拍攝大綱,鐵西區(qū)最讓他癡迷的地方有三個,這三個地方正好可以組成拍攝的主體——工廠、鐵軌、艷粉街。王兵決定就用這三個場景來概括整個鐵西區(qū),這三個地區(qū)也正好是鐵西區(qū)特點(diǎn)最為鮮明的區(qū)域。
但在真正拍攝《鐵西區(qū)》的過程中,王兵其實(shí)并沒有按照區(qū)域的遞進(jìn)順序來拍攝。攝影師出身的王兵,隨機(jī)性的在鐵西區(qū)內(nèi)尋找最好的景深和景別。王兵是個謹(jǐn)慎又謹(jǐn)慎的人。他不與拍攝對象接觸,原因之一是性格內(nèi)斂,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因為王兵害怕有阻力影響紀(jì)錄片的拍攝——他十分清楚鐵西區(qū)這個事物本身對于某些東西來說是消極的、負(fù)面的和不想讓其呈現(xiàn)的。“我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在想什么,也不能讓別人看出來我所要拍攝影片的整體意圖。在拍攝的一年半之中,這個影片只能在我內(nèi)心里一點(diǎn)一點(diǎn)來實(shí)現(xiàn),也只有這樣,我才能安全的將這部影片拍攝完成。”
王兵拿著DV在鐵西區(qū)的寒風(fēng)里站立了18個月,拍了300多個小時的影像。他拍下了空置已久的廠房、不再轟鳴的機(jī)器、雪泥黃冰枯樹灰草混雜在一起的街道,在王兵的鏡頭下,被宣布解雇的工人們,沉默著來到遠(yuǎn)郊的工人療養(yǎng)院治療自己因為長年累月在車間勞作而鉛中毒的身體。這些身份被體制剝奪的人們,在療養(yǎng)院里打牌,情緒來了吹吹薩克斯、看看黃色電影和綜藝節(jié)目。工人們會在下雨時突然安靜的坐下來看雨水,即便是抬著工友淹死的尸體,這些被拋棄的工人們依舊會有一絲凄楚的笑容掛在臉上。他們的生活第一次被做成影像拍攝下來,社會轉(zhuǎn)型期的陣痛從沒有如此近距離的接觸到攝影機(jī)。當(dāng)被解雇的工人等不到所謂的補(bǔ)貼,而被迫去廢棄的工廠里撿拾已經(jīng)變成破銅爛鐵的機(jī)器零件變賣時,工人所期待的只有和工友聚在一起唱唱KTV,唱唱古巨基的《許愿》和董文華的《春天的故事》。
2003年,《鐵西區(qū)》徹底完成。但王兵并不能讓這部電影進(jìn)入國內(nèi)的院線,因為它是一部王兵自己獨(dú)立制作的紀(jì)錄片,沒有審批也沒有許可。王兵只能像所有獨(dú)立紀(jì)錄片導(dǎo)演一樣,拿著《鐵西區(qū)》去國外的影展上碰運(yùn)氣。2003年,《鐵西區(qū)》入選德國柏林電影節(jié)青年論壇,在柏林電影節(jié)青年論壇上的放映結(jié)束后,王兵的《鐵西區(qū)》引起了國際紀(jì)錄片界的重視。同年,王兵紀(jì)錄片處女作《鐵西區(qū)》獲得了紀(jì)錄片界最重要的一個獎項——日本山形國際紀(jì)錄片電影節(jié)“最佳紀(jì)錄片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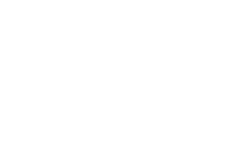
《和鳳鳴》
“歷史是必須要被尊重和呈現(xiàn)的”
但《鐵西區(qū)》的名聲并沒有換來錢,王兵下一部紀(jì)錄片和他的第一部紀(jì)錄片一樣,依舊找不到任何資金。
2004年,又陷入無事可做狀態(tài)的王兵在飛機(jī)上百無聊賴的讀了朋友送給他一本書——楊顯惠的《夾邊溝紀(jì)事》。作為一個西北人,王兵對發(fā)生在家鄉(xiāng)的那段“反右”和勞改農(nóng)場的黑色歷史感到了無比的震驚。這不同于《鐵西區(qū)》的故事,它比《鐵西區(qū)》更為殘酷和富有沖擊力。王兵沒有想到一個運(yùn)動不僅能讓人下崗、失去工作和沒有生氣,還能夠讓人吃人、讓人吃別人的嘔吐物,甚至讓人今夜還在但明早便成為被被子裹著扔到荒地的死尸。
下了飛機(jī)后,王兵心緒澎湃,他把《夾邊溝紀(jì)事》這本“在中國文學(xué)上是至關(guān)重要的”書牢牢記在了心里。王兵去圖書館查閱了大量夾邊溝的資料,后來聯(lián)系到了楊顯惠本人。王兵和楊顯惠聊了很久,楊顯惠書中和口中那些鮮活的歷史,讓王兵覺得“感受到了那個時候的人的一些真實(shí)的心理,他的情感,包括他的身體(狀況)。看到這些聽到這些,我仿佛可以回到50年前。”
2005年,王兵和楊顯惠已經(jīng)多次溝通,決定要把《夾邊溝紀(jì)事》拍成一部故事片。但僅憑一本書來拍攝故事片,對于王兵來說資料并不充裕。《鐵西區(qū)》的拍攝塑造了王兵必須要深思熟慮后再動手的習(xí)慣,不能如此草率的就對一段歷史進(jìn)行粗糙的拍攝,王兵希望自己首先必須要了解和進(jìn)入到那段歷史中去。
機(jī)會很快就來了。2005年8月某天的清晨,楊顯惠聯(lián)系王兵,告訴他有一個夾邊溝當(dāng)年的親歷者,要不要去看看。王兵激動不已,他當(dāng)即拿著攝影機(jī)和楊顯惠一起到這個名叫和鳳鳴的老人家中拜訪。和鳳鳴老人見到楊顯惠和王兵后,沒有多說客套話,這位急需傾訴已經(jīng)被塵封歷史的老人即刻便打開了話匣子。在和鳳鳴老人的講述中,王兵與和鳳鳴老人一起經(jīng)歷從建國開始的一切政治風(fēng)暴。在老人娓娓道來的話語中,17歲的和鳳鳴帶著對祖國的期待,積極地投入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她與丈夫一起在某省的日報社做新聞記者工作。然而時間到了1957年,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了反右傾斗爭運(yùn)動,和鳳鳴的丈夫和她均因欲加之罪被打成右派。和鳳鳴在長年累月的批斗中差點(diǎn)自殺,1958年,和鳳鳴和丈夫分別被強(qiáng)制送往中國西部的兩個勞教農(nóng)場進(jìn)行勞動改造。和鳳鳴老人在農(nóng)場的兩年半時間里超負(fù)荷勞動,饑餓和死亡的陰影一直伴隨著她。
1960年,和鳳鳴的丈夫給妻子寫信,信上說他即將餓死,和鳳鳴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一些吃的,冒著大雪趕到她丈夫勞動的農(nóng)場,然而等待她的只是丈夫已經(jīng)餓死的噩耗。丈夫死后,和鳳鳴老人戴著右派的帽子,帶著兩個孩子茍且偷生地活著,直至1979年被平反。1991年,老人重返自己丈夫死去的勞教農(nóng)場,希望能找到丈夫的墳堆,但和鳳鳴老人最終沒有如愿。
和鳳鳴老人足夠凄慘和悲痛的人生經(jīng)歷,在王兵的腦子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歷史是必須要被尊重和呈現(xiàn)的”成為了王兵至今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但王兵同時深知“歷史是一個很容易變得大而無當(dāng)?shù)脑~語”,要想把《夾邊溝》這樣一個敏感又沉重的題材拍好,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王兵在離開和鳳鳴老人家后,決定先拍攝一部和鳳鳴老人講述自己生平的紀(jì)錄片。王兵花了三天的時間,拍攝了8個小時的素材。王兵讓和鳳鳴老人坐在鏡頭前靜止不動,他用光線的變化來給紀(jì)錄片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和鳳鳴》拍完后為王兵帶來了第二個日本山形國際紀(jì)錄片電影節(jié)獎。王兵隨后又拍攝了講述一個生活貧困但堅持自力更生的農(nóng)民的紀(jì)錄片《無名者》,這期間他接了國外電視臺的命題作文,拍攝了反應(yīng)山西煤礦利益鏈條的《煤炭,錢》。王兵一直在有意克制自己拍攝《夾邊溝》的沖動,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在全國各地尋找夾邊溝的資料和當(dāng)事人,王兵把《夾邊溝紀(jì)事》翻閱過無數(shù)次。《夾邊溝紀(jì)事》里有19個故事,每一個故事在王兵看來都難以取舍。隨著時間的推進(jìn),王兵深知如果再不拍《夾邊溝》,自己可能就要失去一個重現(xiàn)歷史的最佳機(jī)會。

《夾邊溝》
“舊世界分崩離析”
3年對當(dāng)事人的走訪、全國各地尋找到的眾多照片、文字和書信,讓王兵心里拍攝《夾邊溝》的欲望越來越強(qiáng)烈。如果再推遲拍攝計劃,可能那些親歷夾邊溝農(nóng)場黑暗歲月的老人們,會再也無緣見證自己那一段足以寫進(jìn)中國歷史的經(jīng)歷。王兵在迫切的壓力下,決定“主要選取《夾邊溝紀(jì)事》中的三個故事作為基礎(chǔ):《上海女人》、《逃亡》和《一號病房》”,決定了故事,拍攝場地便也定在了這三個故事在小說中發(fā)生的地點(diǎn):甘肅明水。
雖然確定了電影的拍攝內(nèi)容和地點(diǎn),但王兵沒有獨(dú)立執(zhí)導(dǎo)過故事片,他并不清楚帶有王兵印跡的故事片應(yīng)該如何拍攝。在劇本創(chuàng)作的階段,王兵既想讓電影有更豐富的故事性,同時又不想舍棄原始素材的力量。和《鐵西區(qū)》完全不同,王兵不想再用現(xiàn)實(shí)來展現(xiàn)歷史車輪碾壓過后的慘狀,他想要用夾邊溝的勞改這個歷史來叩問歷史本身。在王兵的理解里,紀(jì)錄片和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是“紀(jì)錄片需要線索,而故事片只需要人物”。于是王兵把劇本的核心定位在了人身上,他要展現(xiàn)每一個勞改農(nóng)場內(nèi)茍活、死去和逃出生天的人的狀態(tài)。在第一次看完《夾邊溝紀(jì)事》的6年后,王兵帶著自己對故事片的理解,一個人獨(dú)自寫完了《夾邊溝》的劇本。
因為自己紀(jì)錄片帶來的國際聲望,王兵為《夾邊溝》拉來了法國和比利時的投資。他“沒有花中國人的一分錢”,卻準(zhǔn)備用攝影機(jī)紀(jì)錄中國人最應(yīng)該紀(jì)錄但反而沒有紀(jì)錄的歷史。因為準(zhǔn)備時間充分,王兵組建了對于他來說超大的攝制團(tuán)隊,70個工作人員的陣容,已經(jīng)和《鐵西區(qū)》時單槍匹馬的狀況截然不同。但戲謔的是,導(dǎo)演和執(zhí)行導(dǎo)演以及“百分之八十”的鏡頭依然是王兵一個人完成的。這依舊和王兵孤僻的性格有關(guān),在他看來,拍攝本身就應(yīng)該是自己獨(dú)立完成的事情。在演員的選擇上,王兵沒有更多的資金去用那些已經(jīng)在華語電影圈成名的演員。而是選用了“幾個剛剛畢業(yè)的學(xué)表演的學(xué)生,和唱秦腔、豫劇的。”一切就緒后,王兵帶著攝制團(tuán)隊來到了甘肅。甘肅冬日的天氣極其寒冷,明水當(dāng)年的勞改農(nóng)場是在一片荒地上,于是王兵也帶著攝制團(tuán)隊來到了荒地上。演員們像當(dāng)年的勞改犯一樣,住在人工挖掘的簡陋的土窯子里。這種從荒地上直接挖掘出來四處漏風(fēng)的土窯子,溫度有時比外面還要低。王兵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拍攝著勞改犯們來到農(nóng)場、在農(nóng)場一邊被管教毆打一邊勞作、沒有口糧躺在床上等死和因為饑餓而吃騾馬都不吃的草籽這些當(dāng)年真實(shí)發(fā)生在明水的悲慘事件。
經(jīng)過了三個月的實(shí)拍和一年半的后期制作,《夾邊溝》出爐了。但艱苦拍攝耗盡了王兵的體力,他在拍完這部電影后在家休養(yǎng)至今,就連接受媒體采訪也只能最多聊一個小時左右。《夾邊溝》在拍攝時,便因為題材的原因而獲得了國內(nèi)外媒體的關(guān)注。對于王兵來說,《夾邊溝》以驚喜片的身份入圍第67屆威尼斯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時,他并沒有因此覺得自己又一次成功了。國外媒體的評論證明了王兵的擔(dān)憂,“用紀(jì)錄片的形式講述了一段歷史”和“這其實(shí)還是紀(jì)錄片”的評論讓王兵的故事片無法走出紀(jì)錄片的藩籬。電影中晃動的手持?jǐn)z影、寧靜的長鏡頭和淺淡的敘事線,都讓《夾邊溝》造成的效果也確實(shí)更像《鐵西區(qū)》,而非一部成熟的故事片。
也許王兵永遠(yuǎn)都無法超越《鐵西區(qū)》帶給自己的成功,但正如當(dāng)年王兵在《鐵西區(qū)》的開篇寫的那段話一樣,展現(xiàn)“舊世界分崩離析”永遠(yuǎn)是這個曝光暗處歷史的紀(jì)錄片導(dǎo)演所要拍攝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